父亲90岁了,身体依旧硬朗,神智俱佳,记忆未减。至于眼力,还能轻松自如地穿针呢!就是听力差,不过,这无关衰老,说来有一段故事。

父亲十四岁那年(1946年),把两头小牛放丢了,没敢告诉爷爷。爷爷窜门儿得知此事,怒气冲冲地跑回家,拿出枪来,一边破口大骂,一边冲向父亲的房间。父亲听到叫骂声,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,逃到门后躲避。爷爷一脚踢开父亲的房间门,站在门口对着床开了枪。父亲虽然逃过一劫,但是耳朵被震坏了,右耳接近失聪。
一直知道有这么回事,但是从未听父亲亲口讲过。周六带他去游玩,一路上出于好奇问及此事,了解了详情。讲完了不堪回首的一幕,父亲只是平静地说了句:“你爷爷良心毒得很啊!” “爷爷那么狠心奶奶不骂他吗?” 我不解地问。父亲告诉我, 奶奶是个能干的人,靠着她的勤俭与精算,当初咱们家的生活水平在村里可是首屈一指的。可是,到后来家当都被爷爷败光了。他过份的败家举动免不了遭到奶奶责骂,于是,两人之间战火不断。祸不单行,伯父和叔叔相继患病过世,且两人都在即将成婚的年龄离世。对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来说,这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父亲从没因此怨恨过爷爷。在我的记忆中,爷爷晚年得不到奶奶的谅解,生活没有着落,经常到我家来。他嫌我家伙食太差,跟父亲要钱上馆子,父亲每次都把兜里的钱全掏给他。
父亲是文盲,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了我的母亲。她睿智、贤惠、勤俭、有骨气、知书达礼。两人走过五十一年的风雨历程,父亲没出过一个主意,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劳力者。 有母亲陪伴的五十一年是父亲最幸福的日子,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,亲情的浓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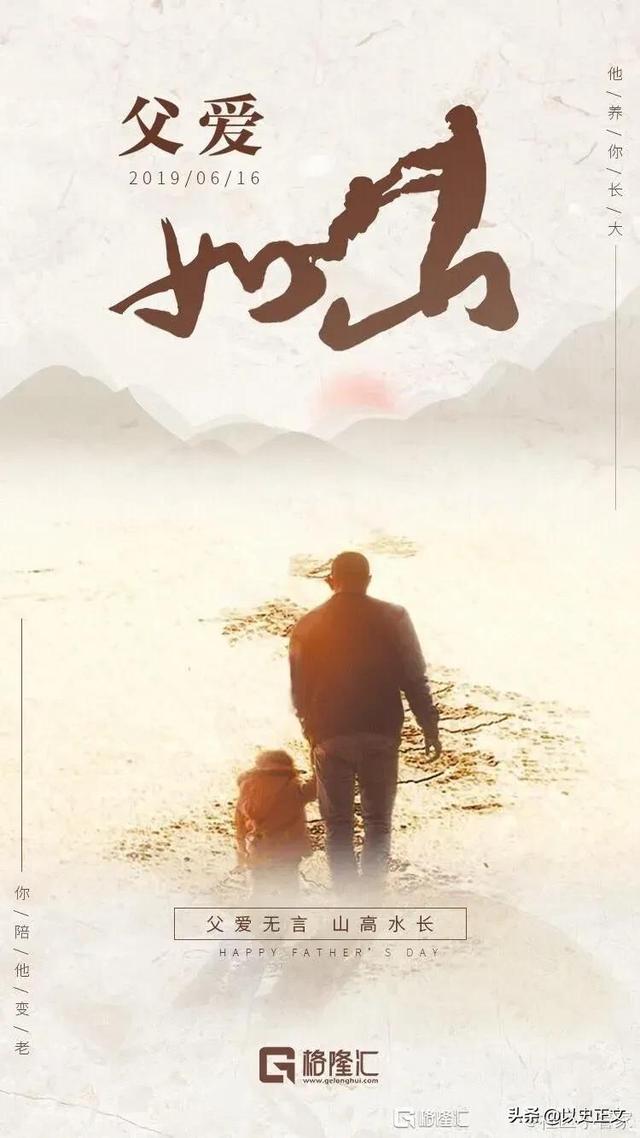
养育7个孩子,赡养4个老人,其间扛活的艰辛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。那时我们村的经济来源全靠男人们上山砍树加工成农具的半成品,扛到城里卖。我们把上山取初料的过程叫做“上箐”。山上荆棘丛生,几十年来父亲从未穿过鞋上山,和他一同上箐的人说,他脚上的老茧,刺见了都得绕开——斗不过。上午八九点钟,村里的男人们三五成群陆续上山,到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人返回了,父亲每天都是上箐队伍里最后返回的。
每当夜幕降临,母亲就焦急万分,带上我们打着手电筒分头沿着上山的路寻找,一路上千呼万唤,听到父亲的回应,悬着的心才能落地,疾步迎上去,欢欢喜喜地拥着父亲回来。有时等到夜里十一二点才接到父亲。那时的我们都胆小,忒怕鬼。走到有坟的路段就再也不敢前行了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魆魆的山峦,有几分惧怕,也有几分亲切……回到家,我们就七手八脚地忙开了——找衣服、端饭菜,端洗脚水……把父亲照顾得妥妥帖帖。
父亲做啥都要做到最好,他弄出的犁(犁田的工具)在整个市场能卖出别人眼中的天价。有时拮据得揭不开锅,母亲拿着大袋子到街上等班车——父亲赶城回来,母亲就有钱买上一大袋子包谷背回家给我们做饭了。每次赶城回来,父亲总要去理个发,然后买上一块五花肉拎回家。煮熟的五花肉切成片放在大碗里,皮色乌亮乌亮的,冒着诱人的香气,再加个蒜泥蘸水,吃起来别有滋味。
街天我们都喜欢跟着父亲上街,因为父亲舍得花钱买大柿子、芭蕉、黄果、荔枝、芒果等稀罕物给我们吃。他牵着我们的手走在街上,见到想吃的果子,我们总忍不住去瞟,父亲牵着我们走过去,蹲到摊前,伸手抓起几个分给我们。我们哪敢去接?连忙推却:“还没给钱呢,我们不要。”父亲不以为然:“吃吧,怕什么呢?钱我装着呢!”我们这才高兴地接过果子大吃起来。
如今,当初那个温暖热闹的大家庭派生为七个小家庭。习惯了热闹享惯了温馨的父亲惧怕孤独,不愿住在乡下,在城里一住就是十多年。白天,他端个小凳到朝阳楼前的小公园享受人气;晚上,他放开“小蜜蜂”听海菜腔唱段。就算我们齐聚一堂,他也习惯吃过饭就回到自己的领地自娱自乐。谈论间提及他,下楼去找,他早已陶醉在海菜腔里了。偶尔给他洗洗衣服,打扫打扫卫生,临走去道个别,他递出一个“好”字就没有下文了。
父亲比较迷信,喜欢去算命,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算命先生留给他的金口玉言。他说算命先生说他余生无忧,兜里随时都有钱,用得快见底时总会有人给他。当然,有时算命先生也怂恿他给我们出难题——拜太岁、叫魂……我们都不信那套,因此弄得父亲长时间闷闷不乐。大姐和大哥换着法子哄,拜太岁、念长寿经……总算让他遂心如意了。
民间有“老小”之说,意为人老了性格往往有还童倾向,孩子气重起来。父亲就如此。母亲过世近20年一直是大姐在照顾他。大姐做得稍不合心他就使性子。有一次,大姐给他夹菜夹多了,他就扔下筷子跑下楼梯口坐着生闷气,发火不吃饭,哄了半天才劝上楼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也逐个成熟起来,走出“心里牵挂着老人,懂得心疼老人就是孝顺”的误区,也学会了“顺”。因此,在身体无恙的前提下,父亲也会脱了些孩子气,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颐养天年。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xiegongwen.com/90092.html






